孔子对于《易》及其卜筮态度
其一,孔子起初只把《易》看作卜筮之书,却并不主张卜筮,认为缺乏智谋的人才频繁卜筮。他以前也是这样教授弟子的。所以,当看到老师“老而好《易》,居则在席,行则在贺”时,作为学生的子赣(即子贡)觉得老师前后矛盾,因而才迷惑不解地询问。孔子不仅指出他理解上的错误,而且耐心地开导他,指出《易》一书产生于“纣乃无道,文王作”的年代,是周文王“讳而避咎”之作,反映了文王的仁义思想(“文王仁”)和忧国忧民意识(“其虑”)。孔子是“乐其知(智)”,赏识蕴藏在《易》一书里的文王之智才“好《易》”的。
其二,孔子“晚而好《易》”,并一度热衷于占筮。这从“吾百占而七十当”一语可以看得出。年轻时不主张占卜的孔子,为什么老了却又热衷于占笟了呢?这大概与孔子50岁后,尤其是在周游列国时所经历的人生坎坷和挫折有关。在到处碰壁、壮志难酬的境况下,孔子一度感到力不从心、吉凶难料,因而不得已利用《易》来占卜,看看运气如何。这其实与他以前所教导学生的“知谋远者,卜筮之繁”也正相吻合。表明即使圣贤,在遭遇坎坷、陷人穷途末路之际,也会一时陷人迷茫而求助于占卜。
其三,一度频繁地占筮使孔子对《易》不时翻阅、详加研究、反复玩味,以至于“韦编三绝”,最终珲解了《易》的本质,从而“不安其用而乐其辞”,即不满足于卜筮而喜欢其文辞了。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,孔子形成了对《易》的全新认识。发现《易》有“古之遗言”,即文王遗教。在孔子看来,“文王仁,不得其志以成其虑。纣乃无道,文王作。讳而辟咎,然后《易》始兴也”。这与《论语•八佾》所记载的孔子关于“周监于二代,郁郁乎文哉,吾从周”之感叹,正相吻合。正是在“古之遗言”里,孔子发现了《易》所蕴含的深刻哲理,即“故《易》刚者使知瞿,柔者使之刚;愚人为而不忘,x人为而去诈”。这也就是孔子所认可的《周易》之“德义”所在。
其四,孔子发现《易》所蕴含的“德义”后,就把“德义”认作《易》之本质,因而放在首要的位置。这从他一再强调“《易》,我后其祝卜矣,我观其徳义耳也”,就可以看出来。尽管如此,孔子也并不否定卜筮,只是把卜筮放在次要的地位,即“我后其祝卜矣”。孔子将《易》的内容大致分为三个层次,即“赞”、“数”、“德”,并认为:“幽赞而达乎数,明数而达乎德,又仁〔守〕者而义行之耳。赞而不达于数,则其为之巫;数而不达于德,则其为之史。史巫之筮,X之而未也,好之而非也。”可见,“德”在三者中域于最高的层次,是《易》的本质之体现。没有达到这个层次均为“史巫之筮”,均未洞悉《易》之思想真髓。
其五,孔子在洞悉《易》的德义本质后,虽然并不否定卜筮,但强调以德行仁义来求福求吉,而把卜筮视为最后的选择:“君子德行焉求福,故祭祀而寡也;仁义焉求吉,故卜筮而希也。祝巫卜筮其后乎。”这与其以前对于弟子关于“德行亡者,神灵之趋;知谋远者,卜筮之繁”的教诲,是完全一致的。可见,在这一点上,孔子学《易》之前与学《易》之后的认识,是一以贯之的。在孔子看来,没有德行的人,神灵也不会去帮助他,所以这种人也不必占筮,诚如《论语•子路》所说:“‘不恒其德,或承之羞。子曰:‘不占而已矣。”
由于孔子晚年特别喜好《易》,以至达到着迷的程度,所以他留下了大量关于《易》的言论,其中的一部分一直保存到现在。它们和其他西汉以前古书中连续记载的有关孔子的文献一样,并非假托,当为《论语》一类的文献。鲜为人知的是,孔子晚年(很可能在68岁返鲁之后),曾对成于他之前的几种《易》文献进行过系统整理和研究,并为之作序。
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《易》残卷附录《易传》六篇,分别是《二三子问》、《系辞》、《易之义》、《要》、《缪和》、《昭力》。据廖名春等学者考证,这些应为战闰中、后期的作品,不会晚于《吕氏春秋》和《韩非子》。在《二三子问》中,记载了孔子与子贡等学生讨论《易》的对话。从以上资料可见,孔子晚年确实喜欢读《易》,认真钻研《易》,以致“韦编三绝”,还向学生传授过《易》。按照传统的说法,认为孔子将他对于《易》的理解作成《十翼》。但是,经后人对《十翼》进行研究,发现其与传统说法不一致,认为《丁翼》大概为孔子口述,由其弟子记载,经过几代传授,到战国中期,才最终成书。
综上所述,根据相关文献,孔子年轻时就接触了《易》,但并未深人研究,不了解《易》的本质,只把《易》视为卜筮之作,自己也断不了占卜,但并不主张频繁卜筮;到50岁后,孔子渐渐喜好《易》,以至于“居则在席,行则在旗。”这里的“行”应该是“出行”、“出远门”,就是外出到当日不能间到住所的地方。统观孔子一生,除了在34岁至37岁“出行”齐国之外,“出行”时间最长的就是周游列国了。由于孔子“好《易》”在其“晚年”,所以,“居则在席,行则在旗”,应该指的是孔子周游列国时期。所谓“韦编三绝”也当是指这期间的情景。这期间(55〜68岁),孔子经历了从“天命之年”到“耳顺之年”的变化,而学习与实践的结合、验证,则使其对《易》的研修也经历了由表及里、由浅人深,由“不知本”到“知本”的过程。使得孔子最终认为《易》的本质在于“徳义”,而非卜筮,因而才说:“《易》,我后其祝卜矣,我观其德义耳也。”“后世之士疑丘者,或以《易》乎?吾求其德而已,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。君子德行焉求福,故祭祀而寡也;仁义焉求吉,故卜筮而希也。祝巫卜筮其后乎。”
综上所述,关于孔子对于《易》及其卜筮的态度,可以大体分为三个阶段:50岁以前,尤其是年轻时,把《易》视为卜筮之作,但并不主张频繁卜筮,也不大相信卜筮;50岁后,尤其是在周游列国期间(55~68岁),孔子渐渐喜好《易》,面对--再遭遇的困厄使其一度热衷于卜筮,但在实践的磨砺和检验中,渐渐认识了《易》之本质,到60岁后就不大卜筮了,并且把《易》视为“德义”之作,即他说“《易》,我后其祝卜矣,我观其德义耳也”,“吾求其德而已”。
孔子这些话,讲得再明确不过了!孔子虽然与“史巫”都应用《易》,都讲卜筮,但最终却同途殊归:“史巫”从中所要的是卜筮之吉凶,而孔子从中所注重的则是“德义”、“仁义”,认为广泛积徳者,没有必要通过祭祀以求福祉;躬行仁义者,没有必要通过卜筮以求吉祥。
但是,时下某些(包括个别“著名易学家”)热衷于借《周易》而宣扬占卜的人,却摘取帛书《要》中“吾百占而七十当”的话,大肆宣扬孔子热衷于占卜。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,是违背史实的。
标签:
本文地址:
/rumen/jichu/130.html
版权声明:本站文章部分来自网络,如有版权问题,请联系删除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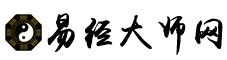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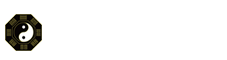


发表评论 (已有0条评论)